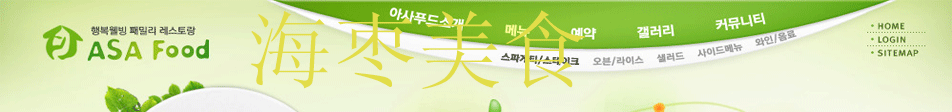|
本文转自:贵州日报 “村BA”现场火热非凡。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杨晓波摄 “村BA”现场,球员演绎精彩。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杨晓波摄 台盘村召开村民代表大会,商讨“村BA”的未来。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王康旭摄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马刚谌晗王康旭 太阳在西山梁子上一晃悠,就快沉了下去,天边的云层变成了斑斓的晚霞。 群峰如幕,倦鸟归飞。台江县台盘村,这个深山苗寨的篮球场上,吴小瑶拍打着篮球投进了几个漂亮的中投,潇洒地跳上滑板滑过球场。 日暮的宁静总会让人心灵平和,吴小瑶特喜欢那柔和又充满希望的光芒,每当这个时候,爸爸妈妈背着掰下的苞谷下山,炊烟四起,锅碗瓢盆汇成交响,这是一家人少有的休憩时光。 “篮球为什么是圆圆的?” “为什么你要和那么多人争来争去呢?” ………… 从记事开始,面对小女儿天真无邪的趣问,父亲吴寿平总是轻抚着她的小脑袋,笑而不语。40年前,也是在夏夜,同样的问题,吴寿平也曾问过自己的父亲吴运权。 日子晃晃悠悠就过去了,当小女儿渐渐长大,不再向他提问,吴寿平也从曾经球场的追风少年,成了肩挑全家生计的顶梁柱,成了那个远近乡邻再熟悉不过的杀猪匠,但这并不妨碍吴小瑶对父亲的崇拜。 往复经年,每到“六月六”吃新节,村里那些熟悉的面容如潮水般归来。外出务工的堂哥搭乘火车返乡,邻居家远嫁的姐姐回来了,为了年年的这一次重逢,苗家女儿们穿上节日盛装载歌载舞,村里的男丁们则相聚在简陋的篮球场捉对厮杀。 只是让吴小瑶没有想到的是,雷打不动的台盘村“吃新节”篮球赛,今年会在全国网民的注视中,掀起阵阵热浪——26个官方账号同步直播,网络直播累计观看人数超过1亿人次,引来外交官赵立坚、中国篮协主席姚明等点赞。 这场球赛,如今被一个新潮又响亮的名字所定义——“村BA”。 这个村落,也拥有了独有的闪亮新标签——“村BA”圣地。 ■热爱绵长,为生活喝彩 8月22日早晨,台盘村篮球场。屏气凝神、调整角度、抖动手腕,“唰”的一声,一记三分球洞穿篮网。 迎着朝阳,岑江龙转身离去。这是村里的“三分王”与村庄间特有的仪式:归来后必到球场投三分示以问候,远行时又以这样的方式聊以告别。 这一天,岑江龙和同村伙伴吴小龙搭乘高铁列车北上遵义,在那,他们将参加为期一周的年贵州省篮球E级教练员培训。 苗乡侗寨的古朴随车窗倒影远去,穿越省城贵阳的绮丽繁华,载着父老乡亲接棒传承的期许,作为“村BA”组织者的一份子,岑江龙、吴小龙此番远行,被村民称为“双龙出海”。 “全省有96个专业篮球教练培训名额,我们村得了两个!学好专业篮球技能就回来,让村里的娃娃们接受更专业的训练。”出发与回归,在“双龙”看来,似乎是一种宿命。 我们无从得知,篮球为何会在台盘村的历史中留下如此深刻的印痕。篮球运动于年首次传入贵州地区,有据可查的台江篮球历史,始于年。 上个世纪,在台盘村全村还没有砖房、瓦房,遍地都是木房的时候,老一辈台盘人小心翼翼摊薄水泥铺在了黄泥巴球场上,村里的木匠伐来木材制成木质框架的篮球架,铁环一钉就是球框。 时光潜流深沉,自那时起,每年“吃新节”,村民都会举办诸如“斗牛”“斗鸟”等传统赛事,因参与度最广、群众最认可,篮球成为了“明星项目”。 篮球运动的狂热,仿佛发育成了台盘人一种“原生的快乐”。球员无大牌、场馆不专业、奖品更谈不上丰厚,打赢了的队伍接着打,打输了的队伍则围坐场边当观众,村民们敲打矿泉水瓶、铝盆应援,呐喊声划破夜空的寂静。 教书的先生,掌勺的厨子,砌砖的泥瓦匠,返乡的大学生……台盘村篮球队的队员,可来自各行各业,他们或以亲情、以友情为纽带,自由组合成队,唯一的要求必须是台盘户籍。 在这其中,绝对的主力当属外出务工又返乡过节的“劳务大军”。数据可知的是,台盘村户人中,外出务工的青壮年劳动力占比近三分之二,绝大多数人的工种都与建筑相关。 当“吃新节”到来,这群离开故土谋求生计,又在节日的召唤中归巢的年轻人们,总要抛下站立在繁华都市各个工地交错的脚手架上负重谋生的重压,回到台盘,赴这一场盛夏之约。 “出去打工是为了找钱,不管找多少钱,都没有回家打球快乐。”作为台盘村球赛的组织者之一,35岁的台盘村民杨雄快人快语,“篮球不能打一辈子,热爱可以!” 同为球赛组织者的村民李正恩颇为认同“快乐”的说法。这些天,李正恩正忙着在田间地头抗旱,他的另一个身份是台盘乡聘用消防员。 除了球赛带来的快乐体验,李正恩更愿意用“自豪”这个词来表达对篮球的热爱:自豪在于,组织好球赛让他收获了乡邻们对其踏实能干的认可;自豪在于,球场角逐,让他在乡土篮球圈里结交了更多的朋友;自豪更在于,篮球运动维系了一种传承,他没有让老一辈人的篮球梦“断代”。 人生的赛场有大有小,“村BA”的球场从不拒绝每一个心怀热爱的篮球爱好者,撕下职业标签,他们都得遵守这里的村规民约和球场规则。 “球场上的规则,就是台盘的村规民约!”村党支部书记张寿双笑谈,“苗族村落过去的族规,是三个‘’,如果有村民犯错,就得交纳斤酒、斤米、斤肉。但是现在,不管球员,还是观众,只要闹事、不尊重裁判,或打架斗殴,都将列入球场黑名单进行曝光,终身不得踏入球场!” 严规在前,并未阻碍台盘村这方小小球场成为快乐的热土。为了让赛事更高效流畅,台盘村人组建了村篮球协会,张开臂膀,欢迎来自全州其他县区近两百支队伍参加竞逐。 “他们就是喜欢我们台盘的篮球氛围,要想在这块球场拿到冠军还是不容易的。”李正恩笑着说,整个赛事期间的控场,都是靠村里年轻人当主力,有的当裁判,有的做安保,有的跑后勤。 小小的台盘村,竟有6个手持篮球裁判证的村民。村民们的自愿集资当作赛事奖金,绝不能动用分毫,而赛事推进的经费来源,则是由村篮球协会向赛场外摆摊的大小摊主们收取,每天几十上百元不等的微薄的收入,转化为盒饭和饮水,支撑着台盘村的赛事组织者们,在一年又一年的球场角逐中接棒传承,甘之如饴。 台盘村骤然爆红后,有市场公司抛出50万的价码,只为在网红球场组织一场赛事,这个消息一时间在台盘村荡起了涟漪,关于“村BA”的未来,两代人有着和而不同的思考。 “我们不搭雨棚,不收门票,不搞商业比赛!”面对外界关于“村BA”商业模式的种种谏言,赛事组织者之一的李正恩摆手重复,用近乎执拗的语气斩钉截铁地“顶”了回去。 “可以赚钱,但不能在球场内!”众声喧哗处,相对年轻的组织者有着更包容的心态,在与杨雄的对话中,我们收获了这一回答:“开发民宿,规范摊位管理,球场外,我们也可以有所作为。” 热度褪去,热爱绵长。当外界以为大红大紫后的台盘村会沉不住气,抓紧把流量“变现”,台盘村老老小小却无一例外地选择了坚守传承:不管靠村民自发募捐集资办赛有多么拮据,在追寻最朴素的快乐的路上,资金不该也无法成为绊脚石。 置身“村BA”红绿配色作底的篮球场,我们迎着看台向上,21步过后,曾经小吃摊林立的晒谷场上,满晒着新收的苞谷。 人生的波折有苦有乐,社会的潮汐有涨有跌,无论时空如何变幻,用双手、用头脑为自己和家人拼搏幸福生活,从来不是高放云端如盖世英雄般的故事。 当村里的年轻人相继背上行囊远走他乡真诚地生活,村庄没有了南来北往的汹涌人潮,也听不见夜以继日的山呼海啸。 宽阔平坦的篮球场状如熨斗,在岁月往复的磨合中,将苗家汉子们在外打拼的那些不为人知的酸楚或是值得分享的骄傲,一一熨平。 ■盛装歌舞,这是我们的主场 “年年六月六,苗家的六月六,请到苗寨走一走,万花开放满枝头,苗家风情醉心头,哎高山青,哎溪水流……” 在台盘村激烈的篮球赛事中,无论是开打之前,还是中场憩息时分,与篮球场相隔不足十米的晒谷场上,苗家妇女着盛装善歌舞,汇成欢乐的海洋。 你很难想象,现代篮球运动与传统民族文化的竞秀与交融,在台盘村呈现出一种反差之美,这种豪迈与柔情的激荡,成为被称为“天下苗族第一县”台江县的独样风情。 在苗族神话传说里,“蝴蝶妈妈”是苗族同胞的始祖和守护神,她被绣在苗家姑娘出嫁时的盛装上,寓意安康和幸福。 与现代机器的简单复制迥异,传统盛装繁复的制作过程,可能需要十几年,因此在母亲的帮助下,苗家姑娘从小就得为自己的嫁妆做准备。 一套盛装嫁衣,历经岁月经纬的缝制,复刻一个民族几百年迁徙的悲壮,不忘来路,才能心有所归,正如这绵延了近一个世纪的篮球传统,同样浸润了苗族妇女们的悉心照料。 “平时我们刷抖音,也发抖音,看到村里的篮球赛几千万人
|